作者:雨后
2025/11/21发表于:SIS001
是否首发:是
字数:3,617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早,也格外猛。北风像刀子一样,透过木门的缝隙钻
进来,即便坐在火塘边,后背也总觉得凉飕飕的。
火塘里的松木噼啪作响,跳跃的火光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明明灭灭,将爷爷
古铜色的脸庞映照得像一尊沉默的雕像,也将母亲低垂的侧脸勾勒出一圈柔和的、
不安的光晕。
爷爷母亲下午刚从老乡那听到父亲消息,说他要除夕才能到家。
我那时年岁尚小,大约十二三的年纪,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手里那个滚烫的烤
地瓜上。地瓜是爷爷下午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在火炭的烘烤下,表皮焦脆,掰
开来,金红色的瓤冒着腾腾的热气,带着一股纯粹的、能慰藉整个寒冬的甜香。
我吃得专注,稚嫩的双手和鼻尖上都沾了黑灰。
爷爷就坐在我对面的矮凳上,他穿着厚重的老棉袄,下身是臃肿的棉裤,脚
边放着他的旱烟袋。他吃地瓜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
目光沉静地望着火塘,仿佛在思考开春后的农事。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木柴的爆
裂声,和我吮吸地瓜的细微声响。
母亲坐在离火塘稍远一些的条凳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手里做着针线
活。她在给爷爷缝补内裤。那是一条洗得发白的、厚棉布做的裤衩,裤腰的松紧
带已经失去了弹性,侧边也磨得有些薄了。母亲的针脚细密而匀称,银针在昏黄
的灯光下穿梭,牵引着灰线,一点点地将那道破绽缝合。她微微低着头,脖颈弯
出一个柔顺的弧度,火光在她乌黑的发髻上跳跃,偶尔能看见她轻轻蹙一下眉,
大概是针脚不够平整。她整个人像是被一层无形的、压抑的纱笼罩着,与这温暖
的火塘格格不入。
不知过了多久,爷爷把手里的地瓜皮丢进火塘,拍了拍手,打破了沉寂:
「乏得很,我回屋炕上躺会儿。」
母亲立刻抬起头,轻声应道:「爹,炕我下午烧过了,应该还热着。」
「嗯。」爷爷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墙壁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他顿了顿,看
了一眼母亲手里的活计,没再说什么,便趿拉着棉鞋,掀开门帘,走进了里屋。
爷爷一走,堂屋里的空气仿佛瞬间松弛了下来。母亲轻轻舒了口气,但手里
的动作并未停下。我则继续享用着我的地瓜,心里盘算着明天能不能再去掏几个
鸟窝。
然而,这份静谧并未持续太久。里屋传来了爷爷低沉而清晰的呼唤,像一块
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
「老大媳妇,」他省略了母亲的姓名,用的是这个家庭里惯常的、带着距离
感的称呼,「缝好了没有?缝好了就拿进来。」
母亲的手明显一抖,针尖险些扎到手指。她朝着里屋方向应道:「还没…
…爹,还差几针。」
「拿进来缝。」爷爷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是一种长期作
为一家之主所形成的、深入骨髓的命令口吻。「屋里亮堂些。」
我看到母亲的脸在火光和灯光的交织下,瞬间变得苍白。她握着内裤的手指
收紧,指节有些发白。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低地应了
一声:「……哎,就来了。」
她放下针线,将那条还未完全缝好的内裤仔细叠好,握在手里,像是握着一
块烫手的山芋。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棉袄的衣襟,动作有些迟缓,又有些难以
言状的慌乱。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似乎想从我这里寻求什么,又或者只是
无意识的一瞥,随即迅速移开,低着头,也掀开门帘,走进了里屋。
门帘落下,晃动着,将两个空间重新隔绝开来。
我起初并未在意,心思还在甜糯的地瓜上。但渐渐地,一种异样的寂静从里
屋弥漫开来。那不是寻常的安静,而是一种粘稠的、仿佛绷紧了的沉默。先前还
能隐约听到爷爷翻身时炕席的吱呀声,或是母亲极低的说话声,但后来,什么声
音都没有了。只有窗外北风掠过屋檐的呼啸,以及火塘里偶尔的一声「噼啪」。
这种寂静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孩子的好奇心像一只小手,在心里轻轻抓挠。
我放下吃剩的地瓜,蹑手蹑脚地走到那扇将堂屋与里屋隔开的木门边。门是旧式
的,门板之间有着宽窄不一的缝隙。我屏住呼吸,将眼睛凑近一道较宽的缝隙,
小心翼翼地望了进去。
煤油灯的光线比堂屋明亮些,将炕上的景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母亲仰面躺在铺着芦苇席的土炕上,棉袄的盘扣被解开了几颗,露出里面月
白色的衬衣领子。她的头发有些散乱,几缕青丝贴在汗湿的额角。爷爷高大的身
躯覆在她之上,他果然只脱了下身的棉裤,上半身还穿着那件厚重的深色棉衣,
此刻衣摆凌乱地掀起。
而他的下身……我的呼吸骤然一窒。他那两条常年劳作、肌肉结实如老树根
般的腿赤裸着,臀部紧绷,而在那腿根之间,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狰狞而硕大的
器官,昂然挺立着,在油灯的光线下泛着暗沉的光泽。它像一件不属于人体的、
充满原始力量的武器,明晃晃地对着身下的母亲,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侵略性。
爷爷的一只粗糙大手,正隔着母亲的衬衣,用力地揉捏着她的胸部。那动作
毫无温柔可言,更像是在检查牲口或者揉搓面团。母亲的脸上交织着痛苦、羞耻
和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迷乱。她微微扭动着身体,双手抵在爷爷坚实的胸膛上,与
其说是推拒,不如说是一种无力的象征性抵抗。
「爹……别……孩子还在外面……」她的声音破碎,带着哭腔,细微得几乎
被心跳声掩盖。
爷爷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呼吸粗重得像拉风箱,另一只手开始用力拉扯母亲
的棉裤腰。「怕什么,」他的声音沙哑而浑浊,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霸道,「缝
个裤子磨磨蹭蹭……老子试试你,是不是也跟这裤腰一样,松了?」
「没有……爹……」母亲的声音带着哀求,身体却在他强势的动作下逐渐失
守。
母亲的屄暴露在了这一方天地内,在爷爷视线里无所遁形,那两片肉颜色已
然有些深了,但内里的屄肉依然粉艳,泛着水灵灵的光泽,周围布满了杂乱无章
的屄毛。
当爷爷沉下腰,将那骇人的鸡巴强行挤进母亲屄里时,母亲发出了一声被死
死压抑住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双腿下意识
地想要并拢,却被爷爷用膝盖粗暴地顶开。
「口是心非的东西……」爷爷喘息着,俯视着身下的人,脸上是一种混合着
欲望和掌控欲的复杂表情,「嘴里说不要,底下这张小嘴,倒是咬得紧。」
这句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母亲身上,她的脸颊瞬间涨红,屈辱的泪水从眼角
滑落,渗入枕巾。然而,她的身体似乎背叛了她的意志,在最初的僵硬和抗拒之
后,我惊恐地发现,她的腰肢开始出现一种细微的、不由自主的迎合。她那原本
推拒的双手,渐渐失去了力气,软软地搭在爷爷的臂膀上。
爷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类似满意的哼声。
「这就对了……」他说道,开始缓慢而有力地耸动臀部,鸡巴不时没入深处隐去
又突然退出一大半,带动着母亲的屄肉翻卷。那动作带着一种农耕时节,用犁铧
深深插入土地般的节奏感和力量感。每一次进入,都仿佛要将压在身下的母亲彻
底贯穿。
「说,是谁的?」他在动作的间隙,威严着问,汗水从他花白的鬓角滴落,
砸在母亲潮红的脸上。
被肏的母亲紧闭着眼,咬着嘴唇,不肯回答。
于是爷爷加重了力道,鸡巴狠狠一顶,炕席发出更剧烈的呻吟。「说!」
「……是爹的……」母亲终于溃不成军,从喉咙深处挤出细若游丝的承认,
带着无尽的羞耻,「都是爹的……」
这声承认仿佛是一剂最强的催情药,爷爷低吼一声,动作变得更加狂野和迅
疾。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耕牛,在属于他的土地上奋力深耕。整个土炕都在他的
撞击下发出有节奏的、不堪重负的摇晃声。母亲的呻吟和哭泣变得断断续续,化
作了婉转的、她自己可能都无法理解的迎合。她的双腿不知何时已经主动盘上了
爷爷粗壮的腰,脚背绷得笔直。
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浓烈的、陌生的腥膻气息,混合着土炕的尘埃味、老人身
上的汗味,以及一种……生命最原始交融的味道。
不知过了多久,爷爷发出一声沉闷如雷的低吼,全身肌肉绷紧如铁,将那生
命的岩浆,猛烈地灌注进最深处。母亲随之发出一声长长的、如同解脱又如同绝
望的叹息,身体像离水的鱼一般剧烈抽搐了几下,然后彻底瘫软下去。
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爷爷伏在母亲身上,粗重地喘息着。片刻后,他支起身体,就着昏暗的灯光,
看了一眼身下狼藉的景象,面无表情地开始擦拭,穿衣。
母亲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双眼空洞地望着被
烟熏黑的屋顶。
而她高潮不断的屄展现了一个属于爷爷鸡巴形状的洞口模样还未愈合,无声
地流淌着白色粘稠的淫夜,狼狈且淫靡。
爷爷提上裤子出来前说了这么一句——等孩子睡着了,你伺候我洗澡。
我猛地缩回头,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跳出来。我蹑手蹑脚地退回
火塘边,重新坐下,拿起那个已经凉透的地瓜,却再也尝不出任何甜味。只觉得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到头顶,比门外呼啸的北风更冷。
我下意识地望向窗外,不知何时,鹅毛般的大雪已经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
无声地覆盖着屋檐、院子和远山。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那么干净,却又那么冰
冷,仿佛要将刚才在里屋发生的那一幕炽热而肮脏的秘密,彻底掩埋。
可是,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看见,就永远也抹不去了。那个冬天,火堆的
温度,地瓜的甜香,与屋内那交织着威严、强迫、屈辱和欲望的淫靡画面,一同
深深地烙进了我年少的记忆里,此后一直阴魂不散,伴随着我成长。
2025/11/21发表于:SIS001
是否首发:是
字数:3,617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早,也格外猛。北风像刀子一样,透过木门的缝隙钻
进来,即便坐在火塘边,后背也总觉得凉飕飕的。
火塘里的松木噼啪作响,跳跃的火光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明明灭灭,将爷爷
古铜色的脸庞映照得像一尊沉默的雕像,也将母亲低垂的侧脸勾勒出一圈柔和的、
不安的光晕。
爷爷母亲下午刚从老乡那听到父亲消息,说他要除夕才能到家。
我那时年岁尚小,大约十二三的年纪,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手里那个滚烫的烤
地瓜上。地瓜是爷爷下午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在火炭的烘烤下,表皮焦脆,掰
开来,金红色的瓤冒着腾腾的热气,带着一股纯粹的、能慰藉整个寒冬的甜香。
我吃得专注,稚嫩的双手和鼻尖上都沾了黑灰。
爷爷就坐在我对面的矮凳上,他穿着厚重的老棉袄,下身是臃肿的棉裤,脚
边放着他的旱烟袋。他吃地瓜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
目光沉静地望着火塘,仿佛在思考开春后的农事。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木柴的爆
裂声,和我吮吸地瓜的细微声响。
母亲坐在离火塘稍远一些的条凳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手里做着针线
活。她在给爷爷缝补内裤。那是一条洗得发白的、厚棉布做的裤衩,裤腰的松紧
带已经失去了弹性,侧边也磨得有些薄了。母亲的针脚细密而匀称,银针在昏黄
的灯光下穿梭,牵引着灰线,一点点地将那道破绽缝合。她微微低着头,脖颈弯
出一个柔顺的弧度,火光在她乌黑的发髻上跳跃,偶尔能看见她轻轻蹙一下眉,
大概是针脚不够平整。她整个人像是被一层无形的、压抑的纱笼罩着,与这温暖
的火塘格格不入。
不知过了多久,爷爷把手里的地瓜皮丢进火塘,拍了拍手,打破了沉寂:
「乏得很,我回屋炕上躺会儿。」
母亲立刻抬起头,轻声应道:「爹,炕我下午烧过了,应该还热着。」
「嗯。」爷爷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墙壁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他顿了顿,看
了一眼母亲手里的活计,没再说什么,便趿拉着棉鞋,掀开门帘,走进了里屋。
爷爷一走,堂屋里的空气仿佛瞬间松弛了下来。母亲轻轻舒了口气,但手里
的动作并未停下。我则继续享用着我的地瓜,心里盘算着明天能不能再去掏几个
鸟窝。
然而,这份静谧并未持续太久。里屋传来了爷爷低沉而清晰的呼唤,像一块
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
「老大媳妇,」他省略了母亲的姓名,用的是这个家庭里惯常的、带着距离
感的称呼,「缝好了没有?缝好了就拿进来。」
母亲的手明显一抖,针尖险些扎到手指。她朝着里屋方向应道:「还没…
…爹,还差几针。」
「拿进来缝。」爷爷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是一种长期作
为一家之主所形成的、深入骨髓的命令口吻。「屋里亮堂些。」
我看到母亲的脸在火光和灯光的交织下,瞬间变得苍白。她握着内裤的手指
收紧,指节有些发白。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低地应了
一声:「……哎,就来了。」
她放下针线,将那条还未完全缝好的内裤仔细叠好,握在手里,像是握着一
块烫手的山芋。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棉袄的衣襟,动作有些迟缓,又有些难以
言状的慌乱。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似乎想从我这里寻求什么,又或者只是
无意识的一瞥,随即迅速移开,低着头,也掀开门帘,走进了里屋。
门帘落下,晃动着,将两个空间重新隔绝开来。
我起初并未在意,心思还在甜糯的地瓜上。但渐渐地,一种异样的寂静从里
屋弥漫开来。那不是寻常的安静,而是一种粘稠的、仿佛绷紧了的沉默。先前还
能隐约听到爷爷翻身时炕席的吱呀声,或是母亲极低的说话声,但后来,什么声
音都没有了。只有窗外北风掠过屋檐的呼啸,以及火塘里偶尔的一声「噼啪」。
这种寂静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孩子的好奇心像一只小手,在心里轻轻抓挠。
我放下吃剩的地瓜,蹑手蹑脚地走到那扇将堂屋与里屋隔开的木门边。门是旧式
的,门板之间有着宽窄不一的缝隙。我屏住呼吸,将眼睛凑近一道较宽的缝隙,
小心翼翼地望了进去。
煤油灯的光线比堂屋明亮些,将炕上的景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母亲仰面躺在铺着芦苇席的土炕上,棉袄的盘扣被解开了几颗,露出里面月
白色的衬衣领子。她的头发有些散乱,几缕青丝贴在汗湿的额角。爷爷高大的身
躯覆在她之上,他果然只脱了下身的棉裤,上半身还穿着那件厚重的深色棉衣,
此刻衣摆凌乱地掀起。
而他的下身……我的呼吸骤然一窒。他那两条常年劳作、肌肉结实如老树根
般的腿赤裸着,臀部紧绷,而在那腿根之间,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狰狞而硕大的
器官,昂然挺立着,在油灯的光线下泛着暗沉的光泽。它像一件不属于人体的、
充满原始力量的武器,明晃晃地对着身下的母亲,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侵略性。
爷爷的一只粗糙大手,正隔着母亲的衬衣,用力地揉捏着她的胸部。那动作
毫无温柔可言,更像是在检查牲口或者揉搓面团。母亲的脸上交织着痛苦、羞耻
和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迷乱。她微微扭动着身体,双手抵在爷爷坚实的胸膛上,与
其说是推拒,不如说是一种无力的象征性抵抗。
「爹……别……孩子还在外面……」她的声音破碎,带着哭腔,细微得几乎
被心跳声掩盖。
爷爷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呼吸粗重得像拉风箱,另一只手开始用力拉扯母亲
的棉裤腰。「怕什么,」他的声音沙哑而浑浊,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霸道,「缝
个裤子磨磨蹭蹭……老子试试你,是不是也跟这裤腰一样,松了?」
「没有……爹……」母亲的声音带着哀求,身体却在他强势的动作下逐渐失
守。
母亲的屄暴露在了这一方天地内,在爷爷视线里无所遁形,那两片肉颜色已
然有些深了,但内里的屄肉依然粉艳,泛着水灵灵的光泽,周围布满了杂乱无章
的屄毛。
当爷爷沉下腰,将那骇人的鸡巴强行挤进母亲屄里时,母亲发出了一声被死
死压抑住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双腿下意识
地想要并拢,却被爷爷用膝盖粗暴地顶开。
「口是心非的东西……」爷爷喘息着,俯视着身下的人,脸上是一种混合着
欲望和掌控欲的复杂表情,「嘴里说不要,底下这张小嘴,倒是咬得紧。」
这句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母亲身上,她的脸颊瞬间涨红,屈辱的泪水从眼角
滑落,渗入枕巾。然而,她的身体似乎背叛了她的意志,在最初的僵硬和抗拒之
后,我惊恐地发现,她的腰肢开始出现一种细微的、不由自主的迎合。她那原本
推拒的双手,渐渐失去了力气,软软地搭在爷爷的臂膀上。
爷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类似满意的哼声。
「这就对了……」他说道,开始缓慢而有力地耸动臀部,鸡巴不时没入深处隐去
又突然退出一大半,带动着母亲的屄肉翻卷。那动作带着一种农耕时节,用犁铧
深深插入土地般的节奏感和力量感。每一次进入,都仿佛要将压在身下的母亲彻
底贯穿。
「说,是谁的?」他在动作的间隙,威严着问,汗水从他花白的鬓角滴落,
砸在母亲潮红的脸上。
被肏的母亲紧闭着眼,咬着嘴唇,不肯回答。
于是爷爷加重了力道,鸡巴狠狠一顶,炕席发出更剧烈的呻吟。「说!」
「……是爹的……」母亲终于溃不成军,从喉咙深处挤出细若游丝的承认,
带着无尽的羞耻,「都是爹的……」
这声承认仿佛是一剂最强的催情药,爷爷低吼一声,动作变得更加狂野和迅
疾。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耕牛,在属于他的土地上奋力深耕。整个土炕都在他的
撞击下发出有节奏的、不堪重负的摇晃声。母亲的呻吟和哭泣变得断断续续,化
作了婉转的、她自己可能都无法理解的迎合。她的双腿不知何时已经主动盘上了
爷爷粗壮的腰,脚背绷得笔直。
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浓烈的、陌生的腥膻气息,混合着土炕的尘埃味、老人身
上的汗味,以及一种……生命最原始交融的味道。
不知过了多久,爷爷发出一声沉闷如雷的低吼,全身肌肉绷紧如铁,将那生
命的岩浆,猛烈地灌注进最深处。母亲随之发出一声长长的、如同解脱又如同绝
望的叹息,身体像离水的鱼一般剧烈抽搐了几下,然后彻底瘫软下去。
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爷爷伏在母亲身上,粗重地喘息着。片刻后,他支起身体,就着昏暗的灯光,
看了一眼身下狼藉的景象,面无表情地开始擦拭,穿衣。
母亲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双眼空洞地望着被
烟熏黑的屋顶。
而她高潮不断的屄展现了一个属于爷爷鸡巴形状的洞口模样还未愈合,无声
地流淌着白色粘稠的淫夜,狼狈且淫靡。
爷爷提上裤子出来前说了这么一句——等孩子睡着了,你伺候我洗澡。
我猛地缩回头,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跳出来。我蹑手蹑脚地退回
火塘边,重新坐下,拿起那个已经凉透的地瓜,却再也尝不出任何甜味。只觉得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到头顶,比门外呼啸的北风更冷。
我下意识地望向窗外,不知何时,鹅毛般的大雪已经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
无声地覆盖着屋檐、院子和远山。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那么干净,却又那么冰
冷,仿佛要将刚才在里屋发生的那一幕炽热而肮脏的秘密,彻底掩埋。
可是,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看见,就永远也抹不去了。那个冬天,火堆的
温度,地瓜的甜香,与屋内那交织着威严、强迫、屈辱和欲望的淫靡画面,一同
深深地烙进了我年少的记忆里,此后一直阴魂不散,伴随着我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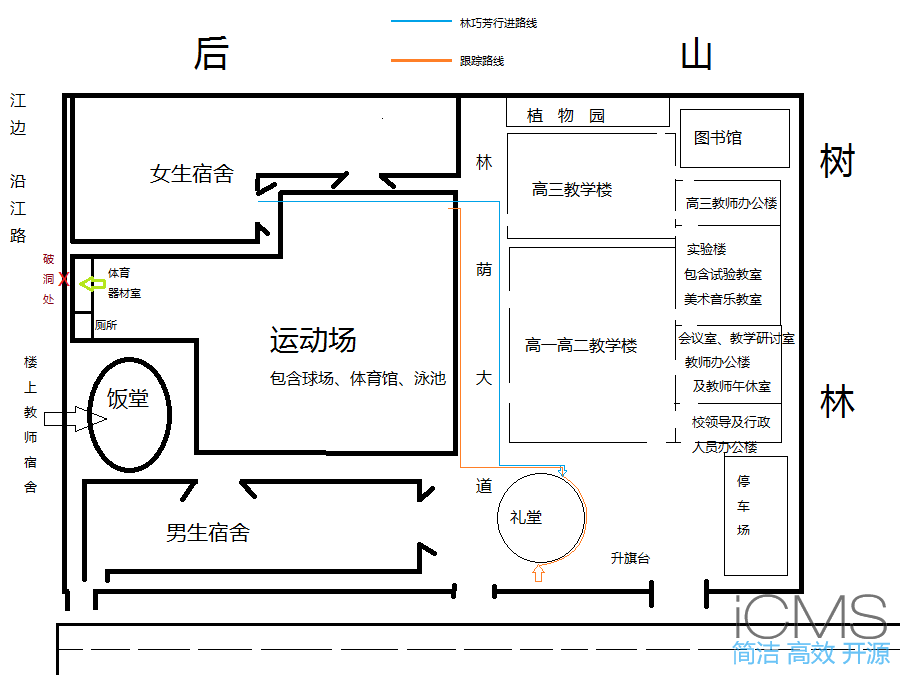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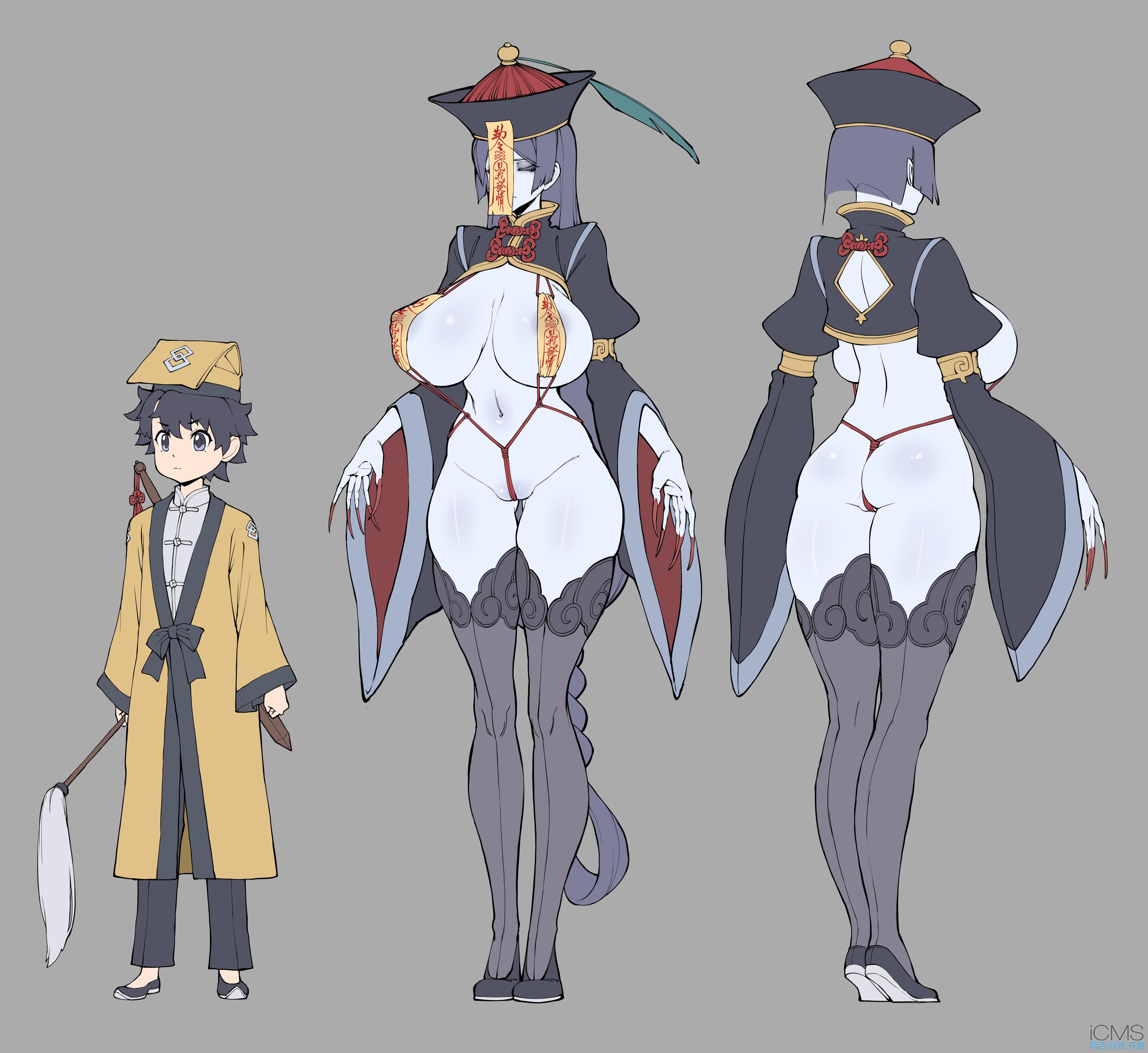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